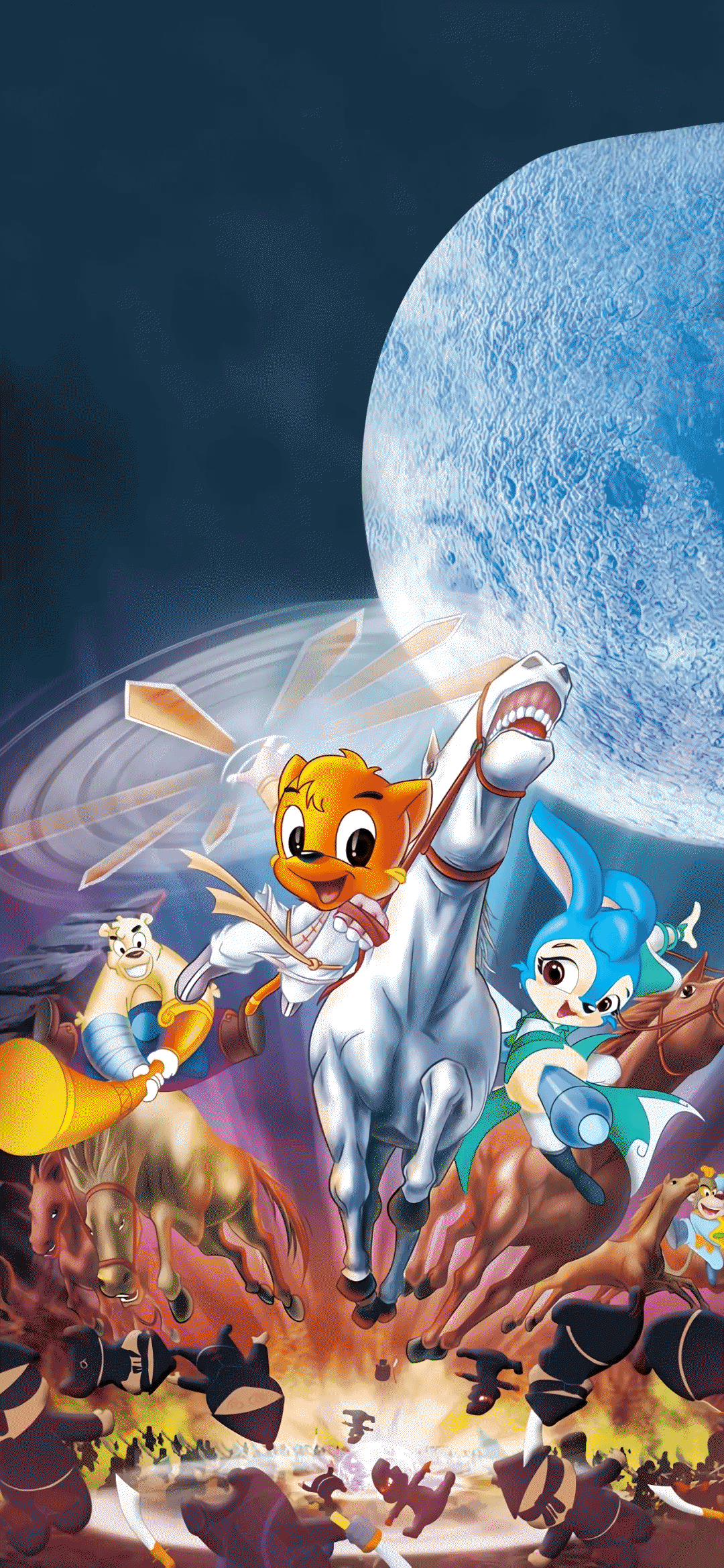![]()
朱鸿兴双浇:虾仁、焖肉。
苏州人早晨出外吃面的习惯,由来已久。苏州博物馆有一块光绪三十年《苏州面馆业各店捐输碑》,记载了当年苏州生意最好的几十家面馆:观正兴、松鹤楼、正元馆、义昌福、陈恒錩、南义兴、北上元万和馆、长春馆、添兴馆、瑞必馆、陆兴馆、胜兴馆、鸿元馆、陆同兴、万与馆、刘兴馆、泳和馆、上淋馆、增兴馆,风林馆、兴兴馆、锦源馆、新德馆、洪源馆、正源馆、德兴馆、元兴馆、老锦兴、长兴馆、陆正兴、张锦记、新南义兴,瑞安楼……可见当时苏州面馆的兴盛,街巷都有面馆了。
这些面馆业者最初可能是肩挑骆驼担子,风里雨里敲着笃笃梆子穿街过巷卖面人,积下来的辛苦钱开间门面,由此白手兴家,皮市街的张锦记就是这样发家的。莲影《苏州小食志》云:
皮市街狮桥旁张锦记面馆,亦有百余年历史者,初,店主人挑一馄饨担,以调和五味咸淡得宣,驰名遐迩,营业日形发达,遂舍挑担生涯,而开面馆焉。
面馆既开之后,焖肉大面汤味清隽,深得新旧顾客喜爱,相传三四代不衰。张锦记亦名列光绪年间的《苏州面馆业捐输碑》中,是苏州面馆的老字号。
![]()
老张锦记这样的面担子,如今间或还能觅得。
张锦记店主最初挑的馄饨担子,苏州俗称骆驼担子,一头是锅灶,后头上搁置各种调味料与碗匙筷子,其下有抽屉数层,分置馄饨与面条,最下格放置汤罐,内有原汤与焖肉,洗碗的水盒与用水则悬于担外,叫卖敲的梆子则绑在前头灶脚下,两头以扁担相连,其上有薄木板凸起似驼峰,故名。或因担子过沉重,挑担者负荷似骆驼而名之。
苏州的面以浇头而论,种类繁多。所谓浇头,是面上加添的佐食之物。所有的面基本上都是阳春面,也就是光面。所谓阳春,取阳春白雪之意,非常雅致。阳春面加添不同的浇头而有焖肉、爆鱼、炒肉、块鱼、爆鳝、鳞丝、鳝糊、虾仁、卤鸭、三鲜、十景、香菇面筋等。所有浇头事先烹妥置于大盆中,出面时加添即可。另有过桥,材料现炒现爆,盛于一小碗中与面同上,有蟹粉、虾蟹、虾腰、三虾、爆肚等等,不下数十种。
![]()
苏州面的浇头,不下数十种。
由于食客习惯喜好不同,同一种浇头又分成不同的类别。朱枫隐《苏州面馆花色》云:
苏州面馆中多专卖面,然即一面,花色繁多,如肉面曰带面,鱼面曰本色。肉面之中,又分肥瘦者曰五花,曰硬膘,亦曰大精头,纯瘦者曰去皮、曰瓜尖,又有曰小肉者,惟夏天卖之。鱼面中分曰肚当,曰头尾,曰惚水,曰卷菜,双浇者曰二鲜,三浇者曰三鲜,鱼肉双浇者曰红二鲜,鸡肉双浇者曰白二鲜,鳝丝面又名鳝背者。面之总名曰大面,大面之中又分硬面烂面,其无浇头者,曰光面,曰免浇。如冬月恐其浇头不热,可令其置于碗底,名日底浇,暑月中嫌汤过烫,可吃拌面,拌面又分冷拌热拌,热拌曰鳝卤、肉卤拌,又有名素拌者,则镇以酱麻糟三油拌之,更觉清香可口。其素面暑月中有之。卤鸭面亦暑月有之。面亦有喜葱者曰重青,不喜葱者则曰免青,二鲜面又曰鸳鸯,大面曰大鸳鸯。凡此种种面色,耳听跑堂口中所唤,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。
由此可见苏州人吃面的讲究了。苏州面的浇头种类虽多,普遍的则是爆鱼和焖肉两种,爆鱼以阳澄湖的青鱼炸氽而成,至于焖肉面的浇头,选用猪肋肉加盐、酱油、绵糖与葱姜斟酒,以文火久焖而成。
![]()
同得兴白汤枫镇大面。
苏州面用的生面,最初是各面馆自制银丝细面。银丝细面细而长,韧而爽,久煮不糊不坨,条条可数。煮面用直径三尺的大镬,黎明时分镬中水初滚,面投水中,若江中放排,浮于波上,整齐有序。再沸之后,即撩于观音斗中,观音斗上圆下尖,最初为观振兴所刨,面入斗中,面汤即沥尽,倾入卤汤碗中,盛若鲫鱼背,然后撒葱花数点,最后添上浇头即成。最早入锅的面汤净面爽,所以苏州人有黎明即起,摸黑赶往面店,为的是吃碗头汤面。
![]()
银丝细面细而长,韧而爽,久煮不糊不坨,条条可数。
银丝细面民国以后改用机制,各面馆应用起来格外方便。不过,1949年后,新乐面馆异军突起,改用小宽面,各面馆争相效尤,连老字号的观振兴、朱鸿兴也用小宽面,小宽面入碗成坨,口感不爽,近十余年又恢复银丝细面。一种饮食传统经年累积,众口尝试已成习惯,不是轻易可以变更的。不过,小宽面并未废置,仍用于夏季的风扇凉面,过去凉面以电扇吹凉,故名。苏州的凉面皆用小宽面制成,也是一种饮食的传统。
![]()
苏州的风扇凉面皆用小宽面制成,也是一种饮食的传统。
苏州的面基本都是阳春面加浇头,面的高下,在于汤底,面汤分红白两种,红汤以不同的浇头卤汁,掺高汤与不同作料,和料酒、绵糖调制而成,汤成褐红色,红汤的高下则在于浇头的烹调工夫。白汤出于枫桥大面,枫桥大面即枫桥的焖肉面,其汤底以鳞鱼与鳝鱼骨再以酒酿提味熬成,江南初夏是鳝鱼盛产期,端午前后,各面馆就挂起枫桥大面的幌子。
![]()
苏州的面,汤分红白两种,红汤以不同的浇头卤汁,掺高汤与不同作料和料酒绵糖调制而成;白汤出于枫桥大面,汤底以鳞鱼与鳝鱼骨再以酒酿提味熬成。
红汤色重香醇,白汤则汤清味鲜,除红白两种汤外,还有昆出奥灶面的汤,奥灶馆创始于咸丰年间,在昆山玉山镇半山桥,初名天番馆,后更名为复兴馆。光绪年间,由富户女佣颜陈氏接手经营,以爆鱼面驰名.其制爆鱼将活鲜的青鱼均匀切块,以当地的菜子油炼成红油.炸爆鱼剩余物的鱼鳞、鱼鳃、鱼血以至青鱼的黏液加作料秘制而成汤,甚得远近食客的喜爱,生意兴隆,因而引起附近面馆的妒忌,称其面“奥糟”,“奥糟”为吴语“龌龊”之意,其后颜陈氏竟将面馆更名奥灶馆,面为奥灶面。
![]()
今日昆山奥灶馆。
虽然汤分红、白,面用银丝,然而各面馆仍有其招牌面,如观正兴的蹄髈面著名于时,其蹄髈浇头焖得肉酥味香,入口即化,且以焖肉的汤作汤底,汤醇香滑,傍晚时分的焖蹄面最佳,金孟远《吴门新竹枝词》云:
时兴细点够肥肠,本色阳春煮白汤。
今日屠门得大嚼,银丝细面拌蹄髈。
咏的就是观正兴的焖蹄面。炒肉面出于黄天源。黄天源是著名的老糕团店,专卖糕团,兼营面点,或谓当年有一熟客每日来店吃面,照例一碗阳春面,一粒炒肉团子,炒肉团子苏州夏令名点,以熟的白米粉裹炒肉馅,炒肉馅以鲜肉为主,辅以虾仁、扁尖、木耳、黄花剁碎炒成,中加卤汁,现制现售。客人以炒肉团馅作浇头,其后黄天源以炒肉为浇头的炒肉面流传至今。
![]()
黄天源炒肉面,以熟的白米粉裹炒肉馅,炒肉馅以鲜肉为主,辅以虾仁、扁尖、术耳、黄花剁碎炒成,中加卤汁,现制现售。
至于咸菜肉丝面,则出于渔郎桥的万泰饭店。万泰饭店创于光绪初年,善调治家常菜饭,其面点著名,尤其开阳咸菜肉丝面为其所创。金孟远《吴门新竹棱词》云:
时兴菜馆铷家常,六十年来齿芳芬。
一盏开阳咸菜西,特殊风殊说渔郎。
老丹枫是家徽州面馆,以售徽式面点著称。《吴中食谱》云:
面之有贵族色彩者,为老丹枫之徽州面,鱼、虾、鸡、鳝无一不有,其价数倍寻常之面,而面更细腻,汤更鲜洁,求之他处不得也。
老丹枫更有小羊面与风爪面,他处所无,老丹枫早已歇业,中西市皋桥旁的六宜馆仍在,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了,以爆青鱼尾为浇头,称甩水面。
松鹤楼是苏州饭店的老字号,创于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乾隆御笔亲题的金字招牌仍在,过去亦以面点著名,在光绪《苏州面馆业捐输碑》名列第二,仅次于观正兴,其卤鸭面最有特色。《吴中食谱》云:
每至夏令,松鹤楼有卤鸭面,其时江村乳鸭未丰,而鹅正到好处,寻常菜馆多以鹅代鸭,松鹤楼曾宣言,苟若证其一腿之肉为鹅非鸭者,客责如何?应之所以如何。然其面不如观正兴、老丹枫,故善食者往市其卤鸭,加他家之面也。
所以至今松鹤楼的卤鸭面仍是过桥,旧时苏州人行雷斋素,吃斋人逢戒斋或开荤,则往松鹤楼吃碗卤鸭面。
![]()
旧时苏州人行雷斋素,吃斋人逢戒斋或开荤,则往松鹤楼吃碗卤鸭面。
虽然各面馆以不同的浇头著名,仍以焖肉面最普遍。焖肉面是大众食品,是苏州面馆的基础,但仍有高下之别。创于光绪十年(1884),位于阊门外帖墩桥旁的近水台以焖肉面著名,苏州人常言近水台的焖肉面“上风吃,下风香”。不过,朱鸿兴的焖肉面却后来居上。朱鸿兴创于民国十七年,原在护龙街(现人民路)鱼行桥旁与怡园相对。其焖肉面最初由店主朱春鹤亲自至菜市选购材料,特选三精三肥的肋条肉制成焖肉浇头,烹调细致,将肉焖至酥软脱骨,焐入面中即化,但化而不失其形。最后浇头与面汤和面融为一体,成中带甜,甜中蕴鲜具体表现苏州面特色,也是姑苏菜肴的特质所在。
![]()
焖肉浇头,烹调细致,将肉焖至酥软脱骨,焐入面中即化,但化而不失其形。
对于焖肉面,我情有独钟。
当年家住仓米巷。仓米巷到现在还是条不起眼的小巷子,但却是沈三白和芸娘的“闲情记趣”所在,芸娘这里表现了不少出色的灶上工夫。出得巷来,就是鹅卵石铺地的护龙街,过鱼行桥不几步,就是朱鸿兴了。每天早晨上学过此,必吃碗焖肉面,朱鸿兴面的浇头众多,尤其初夏子虾上市之时,以虾仁、虾子、虾脑烹爆的三虾面,虾子与虾脑红艳,虾仁白里透红似脂肪球,面用白汤,现爆的三虾浇头覆于银丝细面之上,别说吃了,看起来就令人垂涎欲滴。不过三虾面价昂非我所能问津,当时我虽是苏州县太爷的二少爷,娘管束甚严,说小孩不能惯坏,给的零用钱只够吃焖肉面的,蹲在街旁廊下与拉车卖菜的共吃,比堂吃便宜。所以对焖肉面记忆颇深,离开苏州,一路南来,那滋味常在舌尖打转,虽然过去台北三六九,日升楼宥焖肉面售,但肉硬汤寡,面非银丝而软扒,总不是那种味道。
后来有朋友游苏州归来,告诉我苏州面恢复用银丝细面了。闻之心喜,驿马欲动,四年前的清明前后,少年时在苏州的玩伴联络上了,约在苏州相聚,当年年少十五六,现在都已须发皓然了,于是欣然前往,余兴未了,中秋过后又去苏州,两次前往苏州,都先托朋友订乐乡饭店。乐乡饭店地近北局,转过去就是太监弄,苏州著名的食店集中在此,朱鸿兴也迁来营业。每天早晨奔饭店提供的早餐,穿过北局到朱鸿兴楼上,泡一杯碧螺春,大嚼一碗焖肉面,有时去松鹤楼楼下,吃碗卤鸭面和一客生煎馒头,虽然是蜻蜓点水的逗留,却已慰多年的思念了。
这次在苏州居停三月,苏州的饮食习惯,因社会的转变,已有许多改变,喜的是出门过早吃面的习惯仍在。我来苏州原本无事,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对苏州吃面的习惯作一次考察,饮食文化工作者的田野工作考察比较简单,只要两肩担一口,带着舌头满街走就行了。苏州面馆林立,街巷皆有。我居拙政团后面的北园路,是个僻静的所在,出门就有三家小面馆,出了北园路就是齐门路。齐门路与临顿路相衔,也不是繁华的街道,有朱鸿兴、近水台、蔡万兴分号,这些都悬苏州著名的面馆,而且是百年的老字号,吃起面来很方便。
![]()
朱鸿兴的三浇。
现在苏州的面馆,不论大小,多是长条的板桌,进门买票,然后送到出面处,等待取面,和以往不同,或是当年粮票制度的遗痕。取面处和煮面的灶头,有一块大玻璃相隔,里面工作的情形一目了然,灶上放妥作料的面碗堆砌若金字塔,面自锅中撩起,面汤未尽,即倾入碗,加高汤,然后转至前柜加浇头,各种不同的浇头盛于大号的铝盆中,浇头种类,有焖肉、爆鱼、爆鳝、大排、炒肉、雪菜肉丝等等,然后取面,端烈长条裹上埋头扒食起来,吃罢碗一推,起身就走,倒也迅速利落,不似当年付钱后,堂倌一串吆喝,什么浇头的面,面软或面硬,面浇或底浇,重青或免青,堂内相应,高低有致,而且堂倌报得很快又是苏白,外人很难听懂。不过,却非常热闹有趣,不像现在静静等待取面似排队领口粮,默默扒面似幼儿园排排坐吃果果,人来人往川流不息,甚是沓杂,很难细细品味碗中的面,似牛吃草,了无情趣可言。
![]()
多年前朱鸿兴的水牌。
我在苏州适逢盛夏,一领套头衫,一条短裤,一顶遮阳帽,河人家系舟的所在,朝阳初起,刷了两旁的白墙黑瓦,余下的金屑跌落在河里,化作金鳞片片,一艘清洁河道的木船驶过,船橹摇碎满河的粼粼点点,顷刻又恢复平静,人坐轩中食面,然后捧清茶一杯,观轩外流水逝者如斯,宁静中颇有雅趣。
我们早晨常来吃面,我吃的还是焖肉面,也是偏咸,后来熟了,我要灶上不要太成,但原汤早已炖成,若要不成只有加水,但水添多了汤又寡。于是改吃焖肉爆鳝双浇面。这时正是鳝鱼当令季节,苏州的爆鳝先将活剖的罐鱼腌制下锅炸酥透,然后回锅焐透,香酥鲜甜而无腥昧,和杭州奎元楼的虾爆鳝、无锡聚丰园的脆鳝不同。我往往是焖肉面一碗,爆鳝过桥一小碟,另加切的嫩姜丝一盏,吃时将焖肉与爆鳝焐于碗底,然后将姜丝倾于银丝细面上一拌,此时爆鳝的甜鲜尽出,焖肉的咸味略减,苏州咸中带甜,甜中蕴鲜的风味似可回复几分。
![]()
江南一带独有虾爆鳝面。
一日午睡方醒,想起往来石路,都经过中西市皋桥,石路在闽门外,是观前街外的另一个闹区。老陆稿荐就在桥旁,老陆稿荐是二百年的老店,以酱肉酱鸭闻名,既以酱肉闻名,其焖肉面的汤底一定不错,于是起身驱车前往,当时正是午后,我独占板桌慢慢地吃起焖肉面来,果如我所料,焖肉面的汤不错,但还是咸了些。吃罢面又另带酱肉和糟鹅各一斤,酱肉已不似当年红艳艳入口即化,肥而不腻。夏令正是糟鹅上市的时候,但鹅瘦小如雏鸭,咸而无糟香,姑苏美食竟然至此,可以一叹!倒是出得门来,发现老陆稿荐隔壁就是六宜馆,六宜馆是百年徽州老馆子。不过,现在已经没落了,徽州馆子向以面点精细著名。
第二天我们就去六宜馆晚饭,菜已点妥,我又请老板娘到楼下端碗焖肉面上来,六宜馆楼下长桌数条是卖面点的。面来一试,果然不差,面和汤与焖肉依稀有旧时风味,喜的更是汤不甚成,真的是破落人家留下一只好的旧饭碗,以后再去六宜馆,不论点多少菜,必来碗焖肉面。
![]()
今日同得兴面馆。
吃了这么多焖肉面,临行前不久,突然想到竟遗漏了同德兴面馆。同德兴馆在嘉御坊。于是赶往,老远就看见黄绿底丝边的幌子,中间写了个斗大的面字,随风招展。当时正是午饭时分,入得店来,人声吵杂,挤了半天场买了红汤焖肉丽的面票,然后依红汤白汤两行队伍前去取面,等取了面捧着回来,原先的位子已被人占去,心中甚是不爽,只好在桌角挤了个位子,扒了两口,也没吃出什么味道,就起身出门了。
![]()
红汤焖蹄面。
第二天早晨天下着雨,我又驱车前往,这时早市已过,午饭未至,店里很冷清,我才看清店里的陈设,和他处不同,全是黑漆的八仙桌,长条凳,我拣了个向门对街的座位坐定,要了碗枫桥大面。枫桥大面是白汤的焖肉面,吃了一半,我又要了碗红汤的焖蹄面,堂内不忙,坐柜的小姑娘走了出来问我说:“老师傅,吃得落吗?”答说:尝尝。她说来一两面吧,我说也好。一两是面减半,汤照旧,于我面前摆了两碗面,我吃口红汤的,叉尝一口白汤的,慢慢品尝着,果然名不虚传,确有些旧时风味。我抬起头来,檐下滴着淅沥的雨,檐外行人撑伞匆匆走过,于是,我低头暗暗盘计,来此三月,前后竟吃了近四十碗的焖肉面,真的是饱食终日,惭愧!惭愧!